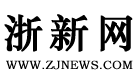张洁琼
北方的秋有些决绝又有点潇洒,她和盛夏分割得明明白白,不带一丝留恋。秋风一起,梧桐叶落,北方就干干脆脆地入了秋。而岛城的秋似乎和夏陷入了热恋,你侬我侬,黏黏糊糊地不肯分别。立秋到了,天气依旧闷热。处暑来了,暑气仍然未消。白露过后,用心感受,晨晚间总算有了微微秋意。岛城的秋,到底是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近了。
秋风是秋最早的使者。晚上要是开着窗睡觉,夜半透过纱窗的风让竹席增添了几分凉意。迷迷糊糊间,深陷甜梦中的人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夏被。要是睡眠有点浅,侧耳静听,树梢间簌簌作响,鏦鏦铮铮。这是西风穿林越梢的声音。第二天清晨抬头看树,栾树率先染上了几分秋色。树梢间栀子黄的花束,热烈地指向旷远的蓝天,拥簇着秋的到来。向阳的枝头仿佛一夜间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似的果实,袖珍可爱。栾树边上的桂花树看上去还毫无动静,但却暗暗积淀着这自然间的能量,孕育着一场独属于秋的绽放。她在等待西风再一次拂过枝叶,一枝盛开则满树竞放、满城飘香。
秋鸿不似春梦了无痕,到底是有了来信。淡蓝的天空不再是只有黄昏时分才有了倦鸟的归林。抬头看天,时不时会有排成队形的鸟群飞过。大概是从北方长途跋涉飞来的大雁、燕子。韦苏州有诗云“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鸿雁和燕子都是北方之鸟,二月北飞,八月则往南来。
此时秋鸿掠过的稻田由青转黄,蛙声随着稻穗的成熟变得无声无息,倒是秋虫成了舞台的主角。盛夏肥胖的知了似乎因为苦夏,瘦了一大圈。但其实夏蝉早已死去,坠入树下,重归土地。此刻叫声凄切独自哀鸣的是新生的秋蝉。灌木丛里,草丛间,砖缝里,秋虫演奏起了奏鸣曲。“居居居居”的是蛐蛐儿,也就是蟋蟀。《诗经》里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和自然的亲昵,让身处钢筋水泥森林的现代人为之汗颜。
夜晚躺在床上凝神分辨,除了蟋蟀声,“唧唧唧唧”是蝈蝈,也就是古人口中的螽斯。“呦呦呦呦”的是油葫芦,“铃——铃——铃”的则是金钟儿。要是叫声再急促点,“铃铃铃”的那就是金铃子。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一位帝王经常夜不能寐,后来不知道从哪得了一方子,“以小金笼捉蟋蟀”放于床下,“夜听其声”。秋虫清亮的鸣叫治好了皇帝的失眠,秋天有声的温柔安抚了那些夜间仍然紧绷的神经。
要是想捕捉到岛城秋天味蕾间的变化,莫过于去清晨的早市逛逛。“秋白鲜红死,水香莲子齐”,欣赏完六月娇艳的荷花,就到了八月起藕收莲子的时节。大的藕比较糯,适合用来做桂花糖藕或是炖排骨汤。小的则可以直接清炒,入口脆甜。手擎着莲蓬,边剥边吃,慢慢咀嚼,唇齿之间似乎还余留着荷花悠长夏日的甜梦。同为“水八仙”的秋菱也到了成熟期,用高压锅烹煮到软糯粉甜,一口气能吃上半盆。秋葡萄已经不似盛夏的青涩酸甜,入口是经过秋露洗礼后的甘甜。鹌鹑蛋大小、青黄相间的秋枣也在流动摊位上占了一席之地,咬上一口,嘎嘣脆。要是碰上卖秋梨的,秋梨老白茶想必是今日的饮茶主题。梨子切成小块放入煮茶壶,用山泉水煮沸。加上秋寿眉做成的老白茶,咕嘟嘟再煮上几分钟。一壶秋梨老白茶,清甜熨帖,可清心可静心,足以抹平繁忙工作带来的疲乏。
秋天的味道也会顺着烤螃蟹的香味爬进海边人家的窗户。立秋一过,秋白蟹就活蹦乱跳地出现在码头上、菜场里。转眼间又张牙舞爪地在家家户户的铁锅里翻腾着。大白蟹烤熟出锅,小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挖开蟹壳,满壳的蟹黄让人垂涎三尺。到了日暮时分,在小院里,在阳台上,摆上一张桌子。吹着秋日的晚风,倒上一碟裕大香醋,咬上一个蟹钳,嘬一口夏日自酿的杨梅烧酒,和家人朋友们边吃边聊。秋日脉脉的温情在谈笑间得以表达。
这样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岛城秋天,我想我是千金不换的。
来源:舟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