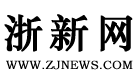咸亨酒店是鲁迅留在绍兴的一个符号,成了多少文人墨客念兹在兹的地方,正因为有了这种文化情愫,在咸亨酒店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关乎文化“好的故事”——
1986年,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学生萧军在咸亨酒店里“小饮于此”,感而赋诗:“咸亨酒店今非昔,座有鸿儒与外宾。忆否当年孔乙己,斯文扫地当‘贼’论。”1989年,著名画家叶浅予一头撞进咸亨酒店,觉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1991年谢晋电影回顾展在绍兴举行,全国影视界、文艺界名流120人会聚咸亨酒店,留下了许多墨宝。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在咸亨酒店酒酣之余,题写“酒逢咸亨千杯少”。著名的文化学者、鲁研专家孙郁先生专门为咸亨酒店写下《绍兴的符号》……
是咸亨酒店与生俱来的鲁迅文化吸引文化名人,还是文化名人的光顾让咸亨酒店的发展更具内涵?二者应该兼而有之。
今天,在咸亨酒店130周岁生日之际,我们就在这一篇篇书写咸亨酒香一样绵长的美文中,感受咸亨酒店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
咸亨酒店一百岁
杜文和
咸亨酒店今年一百岁。
一百年,一个世纪。到了咸亨酒店再一个一百岁的时候,如今这城里活着的,无论大人小孩,到那时候可能就不多了,谁能说咸亨酒店下一个一百岁,他照样可以去店里讨一杯寿酒喝喝?
一缕咸亨酒香,从大清朝光绪年间飘出,曾经飘着飘着就黯然地断了。几扇黑排门沉重地合上,关闭了很久。咸亨酒被历史窖藏起来,再不上市,只是在老人的记忆里留下一点回味。后来鲁迅先生的一杆如椽大笔,将早已冷淡了的咸亨酒重新搅动了一下,竟使得天下沸沸扬扬,都感觉到了咸亨酒的意味悠长,总想着能到绍兴以一种斯文的腔调对着柜台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然后在掌心里排出九文大钱。虽然孔乙己走了: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是坐着用这双手在旁人的说笑声中慢慢走去的。早已走远了,但粉板上还记着他欠下的十九个钱的赊账。稍稍知书识礼的人都想赶到这咸亨来,沉重地便出手将粉板上那十九个钱的赊账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地抹掉。那粉板上挂着的是一件残破的长衫。于是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这一天,关闭了几十年的咸亨酒店又豁然地开了。从大清朝飘来的那一缕酒香,曾经被历史割断了搁置在一边,被灰尘封闭起来,封闭了几十年,也酝酿了几十年,有一种大大异乎昔日的醇美浓烈。这大概也正是绍兴酒的品性。
世纪老店,百年咸亨。自第二次开张起,无须一杆幌子如何招摇,就只在临街的墙上大书一个“酒”字,立时醉人无数。
据学者考证,咸亨酒店现址曾经是一座庙,称旗纛庙,供奉的是一尊旗神。庙中有一颗树,名盖溪树。此树,虽暮春时,叶子仍细小得如枝梢上缀满了苍蝇,因此,别称苍蝇树,但到初秋,凉风一吹,全身树叶转红,火辣辣,就像一面红色大旗。此树又名旗纛树。旗纛树明时已逾千年,高达百尺,粗有五抱,中间是蛀空了的。每年霜降节,人们在这树下“刳羊割豕”,祀拜旗神,很是热闹。但后来旗纛树被大风吹折了主枝,威严就损失了不少,再后来大树被铅弹击中而焚烧,倒下断枝压死三人,从此这地方就冷落了。如今这地方又重新热闹起来,而且盛况空前,虽然旗纛树早已不存,人们心中是祭祀另一尊旗神的。
这当然使我想到了又一件事。
我和我的报社朋友曾经采访过绍兴乡下的安桥头村和皇甫庄,这两个村庄与鲁迅先生都有渊源,这两个村庄都说本地是鲁迅外婆的故乡。有一阵争论得非常激烈。但后来平息了。是不是因为历史的考据发现了不争的事实使得胜负有了确定,还是人们突然地变得豁达大度起来了?是经济的潮流使得人们一贯的观念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他们说:不争了,鲁迅公公没有老钱,如果是争包玉刚的外婆的故乡,那官司打到联合国都是要打的。这见识非常朴实,思维的逻辑也绝不复杂。精神的拥有转变为物质的把握。这是文化的不幸。
文化于生存而言,似乎是十分不济的。
孔乙己穿一件长衫有什么大用?十九文钱的酒账赊在粉板上至今仍不能抹去。
都昌坊口周姓也是世代诗书传家的,但到后来还是破败了,破败到经常出入当铺。
正是在这种生计没有着落的万分窘迫的情况下,绍兴城才出现了一爿咸亨酒店。
文化人本是不屑于买卖的。但终于还是脱下了长衫。京翰林周介孚家的族人准备在都昌坊口张马桥堍这地方开一爿酒店,各家出资,公推秀才周仲翔出任掌柜。这应该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头,垂有一根辫子,颊有微须,消瘦,长衫马褂,举止儒雅。他毕竟是举人的儿子,有着秀才功名,往日以坐馆授徒为业,目前暂无教席,开一爿小小的酒店,带一个徒弟,用一个伙计,日进百把十文想必没有什么问题。周家一族并不指望一爿新开的酒店就能支撑危倾的周家台门,只盼着能够于各家的生计略有小补。周家果然很有学问,很快便从深奥的《易经》中拣出“咸亨”二字,嵌在招牌上,使人觉得不俗,有几分儒家的气息。但酒店的顾客并不很多,纵有一两个也多半是卖苦力的短衣帮,他们并不懂得“咸亨”有着什么样吉祥的意思,他们所关注的是店家有没有往酒里羼水,以及酒提子是否端正了。唯一能将“咸亨”读懂了的只有孔乙己,遗憾的是孔乙己只能在掌心里排出九文大钱,又一次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手上有泥,再就是那粉板上欠着的十九文了。所以周仲翔这个店主当得极不轻松。
在都昌坊口这条当时的冷僻小街上,还有一爿酒店,号“德兴”,为谢姓开设。两爿酒店,一东一西,相隔并不很远,其暗地里的竞争便必然的了。
令满腹诗书的周仲翔不解的是,谢家“德兴”号酒店竟然生意不坏。
周仲翔渐渐支持不住,苦撑了二三年,终于摘下了咸亨的招牌。
于是这门面改由屠家嬷嬷执掌,改成一爿“四不像”的店。“好像是柴店,有塘柴、贡柴;又好像是茶食店,有棋糖、圆眼糖、茄脯、咸梅干;也好像是杂货店,有草纸、火石、火绒、蓝白丝线;还好像是水果店,有小桔子、发红甘蔗、干瘪荸荠、花生、罗汉豆。”并不挂任何招牌。
咸亨酒店消失了,夭折在周家一个老秀才手里。
满腹学问并不能变化为营生的策略,这似乎又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哀了。
然而,咸亨酒店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又重新挂牌开张了,而且再不像先前那样萎缩于一隅,堂堂皇皇于大街上,阔排面,大开间,光彩焕然。酒店前厅青瓦粉墙,条桌长凳,留有当年风貌。后院咸亨楼则另有一番新的气局:庭中金桂飘香,壁画流水环绕;楼上单间或素静雅致,或豪华阔绰。整个咸亨酒店门庭若市,欧洲人、美洲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踵接踵,肩摩肩,络绎不绝。无论海外还是海内的旅客,一旦来到绍兴,似乎不到咸亨坐那么一小会,饮几口绍兴酒,似乎便是一种缺憾。这已成为绍兴的一种风景。
咸亨酒店一天当中曾被前来买醉的客人喝掉5000斤黄酒。
咸亨酒店有近百名员工侍应,仍显得应接不暇。
咸亨酒店有1500平方米的饮食空间,可一次性容纳500人,但拥挤仍成为咸亨酒店亟待改进的“缺点”。
咸亨酒店西首目前又在规划建设一座咸亨旅游城,总投资一个亿。同时,一个以咸亨酒店为核心,由十三家单位组建的咸亨集团也已批准成立。
倒闭前的咸亨酒店与复兴后的咸亨酒店都是使用“咸亨酒店”这同一块招牌。昔日咸亨的冷清寥落乃至破败,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晚清的没落,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时代也就理所当然地该咸亨酒店繁荣呢?国运盛衰与店家前途毫无疑问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新生的咸亨酒店应该端出最陈的酒来感谢一个好时代。
这个时代尊奉鲁迅为“文化的旗帜”,于是周家伯宜公的大少爷周树人,一杆笔将咸亨酒店给救活了,还不仅仅是“起死回生”四个字。北京、上海、杭州纷纷设立的咸亨酒店那是先前所没有的。而且咸亨酒店的分店还将开设到日本等国去。
咸亨酒店今年的营业额将达到800万元。
尽管鲁迅公公没有老钱。
酒店是供人饮食的。
举凡有名的酒店,都必有出众的一两样食物或一两种吃法。
火腿有松柏之香,风鱼有麂鹿之味,醉蛤艳如桃花,醉鲟骨若白玉。碧有莴苣,白有莲藕。这是一种特色。
白腮鲈,杂以冬笋香菇,宽水,薄盐重酒。煮至清,可注砚。这是一种特色。
采芙蓉花,去心蒂、汤焯之,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这是一种特色。
若要厚味,有的有百年老汤。
若要刀工,有的肉片薄能点火。
而恶吃是不足取的。一饮一食,除饱足口腹之外,还应该有另一种更高的享受:或山家清供,使人洒然起山林之兴;或河藕湖莼,使人悠然得水乡之趣。或三杯两盅得亲情的愉悦,或一炉一钵于林下,得独醉的幽想。因此,饮食就进入崇高的文化氛围了。
而咸亨酒店独享盛名,其饱含特色恐怕还是以茴香豆、油炸臭豆腐、爨筒温老酒最为鲜明。咸亨的茴香豆保留了传统的制作工艺,咸亨的油炸臭豆腐使用的是压板豆腐和霉苋菜,咸亨的酒不羼水。
这也是绍兴其他酒店所不难做到的,其中并无不传之秘。
但远道而来的脚步总是纷纷走向咸亨,找一张旧桌买醉。
人们浅斟慢饮,寻找咸亨民俗的、乡土的那一点意思。人们在咸亨品味历史,咀嚼风情,领略故实。
在咸亨可以饮用到文化氛围,这是咸亨的出众处。
咸亨是时代的一处注脚。
咸亨可以找到自己的出典。
本文写于1994年
绍兴的符号
孙郁
绍兴民俗里的古风,因鲁迅的缘故而世人尽知。我最初以为他的小说里许多的地点,不过虚构的产物。后来读知堂的文章,才知道一些地名是古已有之,颇有意思的。我读鲁迅的小说,是在小学五年级,《孔乙己》里的街道、酒店的印象很深,咸亨酒店环境与我生活的那个小镇颇为相似,只是缺乏古韵罢了。于是觉得鲁夫子的故土与自己有点关系,至少那个氛围,是神似得很的。
民国初期,读书人开始注意民俗研究,对乡间谣俗、信仰、礼节等多有心得。那多是用学理的目光,书斋气浓浓,止于观念者为多。唯有鲁迅从形象可感的画面里打捞民风,将生命的气息关注其间,于是诸多风物岁时之态,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便被人记住。比如鲁镇、未庄、咸亨酒店等,内在的味道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既是风俗,又有人情,而后者隐含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百态,似乎成了那里的精魂。
鲁迅夫子真是个高手。他对绍兴街市的描绘只是寥寥几笔,却意象活现。对比民国学人的乡土文本,鲁迅的作品是诗意的存在,恰似旧戏的写意,木刻里的象征,点线间气韵生动。鲁迅同代人写故土的图景多是没有体温的文本,只有知识的意味,殊乏生命价值。我们现在想起咸亨酒店,不仅有茴香豆的香味,孩子的笑声,还有民风里的调子,以及古屋的“乡曲之见”。孔乙己如果不是在酒店里出出进进,那故事如何演绎?换了地方可否?真的不太好说。老舍后来的《茶馆》,也是个北京社会的舞台,那也有与鲁迅接近的存在。只是北京的混浊多多,不及绍兴的清空、静谧了。这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没有办法的。
乡土里有国民的灵魂,那是对的。可是中国乡镇活生生的存在被记录的不多,那原因是没有鲁迅那样大手笔的人物。名胜之名,实乃因人之名而名。它自然是得到了特殊精神的辐射。或由事件,或靠诗文,或因奇人,如此而已。鲁镇的咸亨酒店真的是因鲁迅而声名愈著。它的名字使我们想起《周易》,也念及晚清。但最终因了鲁迅悲悯的个性情怀而注入血液,闪动着幽玄的光泽。《孔乙己》写得简约生动,寂寞人间的故事,饱含着街市的表情。常态里的非常态人生,才是咸亨酒店的见证。鲁迅借着这个酒店,把绍兴的风俗图画得实在精彩。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绍兴,在咸亨酒店聚餐,被其间的氛围所感动。才知道了那里的特殊韵致,好像找到了鲁迅小说的底色之一。那是古镇诗意的遗存,旧梦早已流逝,惟风貌还留在这里。门前的孔乙己雕像,真的传神。这是历史的符号,还是审美的符号?真的说不清楚的。
我喜欢绍兴,自然也喜欢因鲁迅而留下的诸多符号。鲁迅是绍兴的符号,这是不错的。但他留下的符号又在延伸着新的符号。对我来说,现在谈它,关注的是那个晦暝不已的隐含。不仅仅储存着旧时的意象,重要的是精神史的信息。而后者,作为一个象征,提示着我们如何看人,又如何看己。在主奴文化基因浓烈的社会,鲁老夫子给我们的提示,真的太多太多了。
本文写于2010年
咸亨酒店传奇
叶浅予
凡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知道绍兴城中有一家咸亨酒店,是各类下层人物的荟萃之所。一九六一年我初次访问绍兴水乡时,不知鲁迅小说中的那家咸亨在哪条街、哪条巷。事隔三十年,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再次访问绍兴,主人特地安排在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大咸亨里为客人摆午宴,主人还郑重介绍这家咸亨就是鲁迅小说里的真正咸亨,一下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私下问自己:阿Q和孔乙己之类穷光蛋能在这家大字号咸亨里挂账吃酒吗?再一想,北京的恭王府硬被人定为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不也一样使人信以为真吗?大凡小说中的人和物,明白人都知道是假拟或虚构的,一旦被有心人引经据典造出个真人真事来,明白人也不个个是傻瓜,何必费那么多工夫去考证与辨伪。更何况绍兴的街头巷尾,处处有咸亨,门前摆个摊子,卖油炸臭豆腐,是绍兴人爱吃的东西,鲁迅小说里可能提到过,这就是定为真正老咸亨的一个标志。
进了店堂,当作过道的正中一间,两侧两排条桌,每桌两只长凳,坐满酒客,都是短装卷裤腿或赤脚的,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人物,东边一间有门相通,摆的是方桌,每桌可坐四人,酒客的打扮,似乎高一档,无论中间或东间,佐酒的菜一律是茴香豆或水花生。也有手拿一串油炸臭豆腐进店来的。看了这情景,颇想画几笔速写,留下形象资料,但主人已带着客人跨进后院,只得跟进。
后院是个大天井,就地排着十来只未开封的酒坛,侧头看东面有个跨院,靠墙堆满空酒坛,看来这家老牌咸亨生意不错,当经理的绝非庸碌之辈。回过头来,正面是座新建的三层雅座,主人带我们上了楼,也是三开间,中间一间摆了二席圆台面,台面上有转盘,十足的大饭馆气派,转盘上摆好四样下酒菜,茴香豆、水花生、炸臭豆腐、冷香干,是咸亨的老食谱,合我的胃口。再一看,主人打开一大瓶“可口可乐”往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倒,我急忙止之,到了咸亨,不喝陈年花雕而喝可口可乐,不是要笑煞孔乙己吗?拿黄酒来,把玻璃杯换成小酒碗,才像个样。服务员都是穿高跟鞋的年轻姑娘,见我这白须白发老人如此发号施令,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主人会意,赶紧跑下楼去,搬来楼下酒客所用的小酒碗,打开一瓶瓶绍兴加饭酒。主人以为我有酒瘾,为我倒了一满碗,其实我有心脏病,早就戒酒了,哪敢再碰这后劲颇大的加饭,为了护卫我的老面子,装出一副老酒客的样子,勉强举杯和大家一起劝酒,冒险喝了一口,以后就只顾吃菜,不碰酒了,尽管别人也有不喝加饭而喝可乐的,我却道貌岸然,坚决拒绝可乐。
一口加饭下肚,头脑开始晕晕然。咸亨曲尺形柜台前出现了一场传奇好戏:
清代孔乙己缓缓地从土地庙走来,仰头向酒保示意,要了一碗烫热的老酒,一碟茴香豆,独自吃着。
本文写于1989年
陈桥驿
改革开放之初,在一次家乡的宴请中,有一位父母官说:教授有才能,又常常出国,却很关心家乡,值得感谢。这几句话实在让我内疚。因为我生在绍兴,学在绍兴,却一直漂荡外地,没有为家乡服务。所以随即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家乡父母官有什么嘱咐,事事遵办;家乡父老朋友有什么召唤,随传随到。的确,每次回乡,父母官和父老亲友,都逾格厚待,为家乡领导和父老亲朋做点事,当然义不容辞。
记得是1989年岁尾,有个什么会议,我们夫妇应邀住在绍兴饭店。一个清早,有位年轻人叩门来告:今天中午市长请二位到隔壁龙山宾馆吃顿便饭,届时会派人来接。我在领情之下颇感此请有些突然。午前果然有一位中年人到来,当时还不流行名片,自称是什么酒厂的厂长,市长要他前来恭请。
王贤芳市长就在宾馆门口迎接。一个精致的小餐厅,一张小方桌,四个席位,市长和我们夫妇以外,就是这位到绍兴饭店来的厂长。我感到纳闷,为什么市长请客要一位酒厂厂长作陪?
市长在说了几句我有才能、眼界宽和对家乡有贡献之类的客气话以后就转入正题,即明春要举行的“鉴湖纪念会”。他说:此会由水利局主持,局长是教授的学生,教授是鉴湖专家,他不是绍兴人,一点不懂鉴湖,所以决定与会聆听教授和其他专家的高见。有名的绍兴酒是鉴湖水酿造的(到此我才清楚市长请酒厂厂长作陪的原因),那个鉴湖在漓渚(当指赝石、容山诸湖),湖水是洁净而含有特殊物质的。但城内和近郊的水,就污染严重。特别是那爿咸亨酒店,是外宾必到之处,从此店朝西走几步,就是一条污浊的小河。说到此时,话锋又一转,他斜瞥了厂长一眼,然后续言:绍兴酒的国外市场主要是日本,让他们看到城内河水的污染程度,他们不会开口问,我们也无法解释,但绍兴酒的外销必然要受到重大影响。为此,这个“鉴湖会”,我们不邀请外国学者。而据说有些日本学者想来。教授和夫人在日本的威望我们早已知道,所以恳求教授向日本学者做些工作,说明我们此会是个小会,也不讨论鉴湖水做绍兴酒的事,所以不邀请外宾。
父母官的嘱咐,我当然一口应承。而事情也很易办,我只写了一封信给斯波义信教授,因为鉴湖在日本的主要研究者就是他,而且我们之间,谈话和信件来往,都可以用英语解决。我夫人在宴毕返绍兴饭店路上倒是发了点小牢骚:门面不大名气大,也会给人制造麻烦。我告诉他,事不关咸亨,是为政者不重治水之故。我们在京都,不是看到市内小河都清澈见底吗?而咸亨的这“门面不大”倒是应该保持下去,这叫作“原汁原味”。
和“鉴湖会”同年,绍兴的几位学人合作写了一本《绍兴酒文化》的书到上海出版,而要我这个完全不懂酒的人在卷首作《序》。我在《序》中对民间流传和酒楼壁上对绍兴酒的吹嘘之言作了一点批判,说了几句真话。此书传到日本,拙《序》竟受到彼邦人的高度青睐,甚至决定素来由日本主持的“国际酒文化学术讨论会”,1994年的那次到我所在的杭州举行。
事有凑巧,那几年,杭州的浙江工学院聘请了一位日本的客座教授,会务正好由他办理。会前,他曾请该校派人陪同到舍下,告诉我,会址设在西子宾馆,会期三天。并有几条我必须注意的事:一、会议由日本老专家野白喜久雄和我为首,但野白先生因年事较高而近时身体欠佳,所以只好请我偏劳。二、以半天用于开幕式和闭幕式,一天半时间宣读论文,执行主席请我一人偏劳,会议用语是英语。三、会议要出论文集,野白先生和我列名主编,但《序》请我署名执笔(后来于同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94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四、用一天时间外出参观,初步设想是绍兴某个酒厂,中午由会议出资在咸亨酒店为代表们设宴(意思是日方请客),下午游览兰亭等名胜然后返杭。“咸亨酒店午宴”。这是几位父母官都嘱咐过必须谨慎的事,特别是这次的来客不寻常,都是资深的酿酒专家,怎能让他们看到“朝西走几步”的那条浊流呢。“门面小,名气大”的咸亨,这一回真的要给我制造大麻烦了。我考虑了一番才发表意见。因为双方都用英语谈话,可以假装选择英语词汇的形式考虑实在要说的话。或许是急中生智,我立刻想到了余姚,因为那里有一位领导层内的老学生。于是我对这日本教授说:会议安排得基本不错,执行主席和论文集作《序》的事我也可以承担。只是外出参观一天的安排欠妥。代表们多数都从国外来,仅仅一天时间,应该让他们多跑些地方,不能完全锁在绍兴。绍兴酒指的是绍兴一府各邑的酒,何况黄酒酿造是同一个模式,不一定看绍兴的酒厂。兰亭确实是名胜,但现在的兰亭离王羲之集会的兰亭甚远,这方面,我在日本的几所名牌大学都作过演讲。所以外出参观这一天的内容由我来安排奉告。对我能承担这一天参观的事,他有正中下怀之感,站起来对我作日式鞠躬。但加上一句:咸亨的宴会是许多代表提出的,请你仍安排进去,因为这是事前要和店方预订席位的。“咸亨麻烦”临头,但我总得设法摆脱它。
一辈子以粉笔度生的人,唯一的“资源”就是学生。这位余姚市领导层成员的学生随即应召而到,因为此事非面谈不可。我告诉他让这批外国人为主的代表到余姚,是余姚的光荣。参观余姚酒厂,请酒厂中午设宴,下午参观河姆渡,傍晚离开。次日得到的答复比我要求的更好:中午由余姚市长宴请。我立刻告诉这位日本教授,并要他们预订这天晚上的咸亨席位。
会议随即开幕,而那一天的余姚参观,大家都很满意。我夫人当然心里有数,所以对酒厂厂长的讲解,宴会上的市长讲话及河姆渡讲解员的讲解,都慢条斯理地翻译。在河姆渡登上回程车时已经薄暮,到咸亨酒店快晚上九点,想起几位父母官的嘱咐,我感到轻松。大家兴高采烈地上楼。我们学校的校办主任早已等在店堂门口,因为事前说好,次日学校的十几位领导和教授,在绍兴有一个会议,我是不参加最后的闭幕式的。我也邀这位主任及驾驶员一起上楼吃他们的第二顿晚餐,日本人多,所以餐厅上的一切都是日本礼俗,敬酒、谈话,都是静悄悄的,也有不少代表,分批结伴携酒下楼,在店堂上饮酒摄影留念,但也都是轻手轻脚的。或许是茴香豆的缘故,散席已近子夜,店堂全无饮客,只有几位职工挥手向我们告别,其实是等着关门。等到我们送代表们登车离别,回头一看,店门已经关闭了。而好事的校办主任,一定要我们夫妇站在“全封闭”的店门下,为我们摄影留念,然后驱车到杭州大学来客住宿的绍兴饭店。这一晚,为了这个“门面小名气大”的咸亨酒店,实在没有睡上几个小时。
又碰上了一件巧事,我八十岁(2002年)那年,好友车越乔兄夫妇特地从香港赶回绍兴,为我举办一次祝寿大会。又请了懂艺术的人到舍下搜罗了许多照片,为我编印了一册装帧精美的《80华诞影集》。把我老家屋舍以及我们夫妇、子女在国内外的各种活动,分门别类地编列在影集中,而这张“夜半咸亨”,居然也收在其中(127页)。这或许是全集中最单调的一幅了:我们夫妇站在“全封闭”的店前,一面是一块自右自左的招牌“咸亨酒店”。照片下的说明是:“半夜十二点,先生送走三十多位酒文化专家和酿造业主后,与夫人在咸亨酒店合影(已经上牌门了)”。偶然看到这幅照片,颇让我溯昔抚今,不胜感慨。
我希望的是,“门面小”,让它一直小下去,这就是上面说过的“原汁原味”。“名气大”,让它更大起来,这是我们绍兴的一块重要牌子。何况我年已近九,虽然按国家规定不退休,但已经不怕你这块牌子再找我麻烦了。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朝西走几步”的这条浊河,能够成为一条清流。全绍兴的河湖网都能获得化浊为清的整治。本文写于2009年
诗咏绍兴
——咸亨酒店
黄亚洲
这里连时间也好像盐渍过
如狭长的萝卜干
走进这家店,要穿过一个朝代
所有的钟表都开始往回走
不要看门外太阳
太阳肯定在往东面落下
三两碟茴香豆,十数只喜蛋
一会儿,神经就渍咸了
生活原来是这样有滋有味
占领这里的条凳是一种福分
可以用很慢的节拍挖趾甲
挖天气 毡帽 乌篷船
某人与某人如何轧如何闹如何杀
挖咸渍渍的民国初年
师爷 义犬 三姨太
该说的话说了十遍
不该说的也说了三遍
你稳坐江山
不晓得太阳已砸破哪家梁檐
只晓得时间在趾缝里搓落
落在康熙年间
酒保同志又走过来了,笑嘻嘻
把细嘴壶拎成一曲绍兴高调
斟满岁月
这里条凳很宽
宽如中国历史
坐在这里,真的就像坐在龙椅上
你发落一切
所有的朝代都臣伏于地
唯有你的生命在威严滚动
像茴香豆一样,余音不绝
沿着舌头的方向
在“咸亨酒店”
陈忠实
上午游览了东湖,下午又要到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地方去,明天一早就要返回上海了;东湖的山光水色令人赏心悦目,兰亭的幽雅景致也叫人神往。可是,没有到孔乙己曾经喝酒吃茴香豆儿的“咸亨酒店”光顾一番,怎么能算真正到过鲁镇呢?
午休时间,几位朋友相邀,正中下怀。虽然已觉腿酸眼困,仍然兴致勃勃地走出住所的大门。
一幅金字黑匾,老远就赫然入眼,上书:咸亨酒店。平房,黑色小瓦,坐落在街道一边,夹挤在高高低低的楼房中间,自有一副古香古色的神采。门面宽约三四间,木门板全部拔除,整个酒店就完全无遮无挡地当街敞开着。依然保持着当年“鲁镇的酒店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那木板制的曲尺形大柜台,油漆斑驳,木棱也已磨光,探过头去,可以看见赭红色的酒坛。我把钱递了上去。卖酒的是一位中年女人,穿着白大褂,使人觉得有失鲁镇的格局,与那曲尺形的柜台也不协调。她用一只提斗从酒坛里提上酒来,倒入酒杯,黄酒其实是暗红色的液体。这杯子更古朴,用洋铁皮焊接而成,大到可以盛一斤酒,上端粗,下端细,状如漏斗。据说冬天喝酒时,可以把细端塞进热水里,用以温酒。鲁镇的长衫阶层或短衣帮,当年就是用这样的酒杯,孔乙己自然也用这样的铁皮酒杯。
茴香豆也不能不尝一尝。不尝一尝孔乙己津津乐道的茴香豆,也许不算真正地进过“咸亨酒店”呢!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我们刚刚在长条桌边落座,不知谁在拖长声调模仿着孔乙己的名言,摇头晃脑说起来了。木条桌长到丈余,从门口直通到墙根,实际应该算是木案子了。一切遵循孔乙己的习惯,他是穿长衫阶层中唯一站着喝酒的人,于是我们也都站着,他大约用手指捏茴香豆,于是我们也免去了筷子。那用粳米酿成的名曰“加饭”的黄酒,说不准是一股怎样的滋味,既不似白酒那么烈,也没有葡萄酒那么甜,说不上好喝或不好喝,唯其因为孔乙己十分喜好,我拼着将那一杯全然灌下了。那茴香豆也没有多少特色,唯其因为孔乙己喜欢,我们嚼起来,似乎别具兴味。
酒店墙上,有一幅裱饰过的题词,一副对联。题词曰:
上大人孔乙己高朋满座
化三千七十士玉壶生春
对联曰:
小店名气大
老酒醉人多
看看题款,竟是著名作家李凖献辞,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手书。辞联极致幽默的韵味,笔墨亦遒劲潇洒,使古朴的“咸亨酒店”平添了一丝风韵。
孔乙己确实是高朋满座了。小小的酒店里,现在拥拥挤挤坐着的酒客,大都是从南方或北方来到鲁镇而落脚此店的。有穿着西装革履的学者风度的男女;也有一身正统中山装很有派头的干部;更有一帮一伙长发披肩紧绷牛仔裤的青年男女,一律坐着或站着喝着装在洋铁皮酒杯里的“加饭”酒,抓着茴香豆,笑语喧哗……
解放以后,自打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不管其是否特别喜欢文学,大约没有谁会忘却孔乙己的。
孔乙己不属英雄之列,而实实在在是一个被挤扁被碾轧为尘末的迂腐的老夫子,那些主宰鲁镇风云的鲁四老爷之流早该化为污泥了,而独有上大人孔乙己获得了川流不息的朝拜者,真是得其所哉!
摘自陈忠实散文集《父亲的书》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