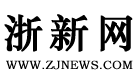柯兰
一幅耕牛图,刻在汉砖上,写在唐诗中,出现在齐白石的名画里,更铭记在每一个曾与牛同甘共苦的日子里。
作为放牛娃,我的童年充满牛的气息、牛的身影。夕阳西下,一头老牛从田野里缓缓归来,身披橙色的光亮,向着家的方向走去。那里有炊烟,有灯火,还有寻常的日子。我与牛相伴相随,每天做着“耕与读”的程序转换。
那时候,对大多数乡邻来说,牛与土地意味着艰苦的劳作。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割,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与牛的艰辛汗水。牛需要有人每天牵着它、养活它,幼小的我理所当然地担当起牧童的“重任”。在走出农村前,我的两脚不但带着田里的泥巴,更多的光阴要与牛相伴。
遥想当年,青草地里,牛在悠然吃草,远方是大雾笼罩的旷野,朦朦胧胧,隐隐约约,透着大自然的神秘和宽广。大部分时间,我把牛散放于青草地。草地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水淙淙流淌。遍布的青草,牛一辈子也吃不完。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辽阔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除了弥漫的大雾,还有就是偶尔飞过的小鸟。牛在啃着青草,草茎被牛锋利的槽牙切断时发出的声音有些悦耳,紧随悦耳之声到来的,是青草甘甜的气息。牛啃草时头一点一点的,与婴儿吸奶的动作几乎相同。啃着啃着,牛忽然抬起头来,望向远方,思考着什么,眼神恍惚,它可能也被漫天的大雾打动了吧,只是它不说出来,继续低头吃草。
我在牛的下风口闻着青草的甜香和泥土的腥气,同样有一种恍惚和陶醉的感觉,这是一种与牛相处的特殊感觉。太阳出来了,雾缓缓退去。
落日的余晖照耀着青草地,田地山川布满金光。牛也吃饱了,该回家了,我骑上牛背,闭眼假寐,牛自会把我驮回村里。它不走弯路,遇着沟坎会放慢脚步,轻轻地跨,悄悄地迈,生怕将我颠下来。到了牛棚前,它站住,打一个响鼻,耸一耸背脊。我把它关进牛棚,独自回家吃晚饭。
谷雨,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开启了种植时间,村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犁节,自然少不了牛这个最重要的主角。一大早,作为村里的第一耕田好手,父亲就将红绸缨系到我精心放养的牛身上,把耕牛装扮一新。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牵着牛,父亲扛着犁,我们一起披着朝霞,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来到早已选定的一块种满草籽的水田旁。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生产队的社员。我跟随父亲来到田边,只见满田的草籽长得十分茂盛,一串串淡紫色的花宛如漂亮的二月兰。草籽花引来无数的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这些草籽经过一冬的生长,即将成为新一年庄稼地里最好的肥料。
父亲牵过牛,架好犁具,打响牛鞭,吆喝一声:“开犁啦!”田边的社员们跟着吆喝,吆喝声以一个春天的多姿,写意着农耕盛事,响彻在田野上空,呼唤着新年的丰收梦想。一人、一犁、一牛,像是一支世间最有活力的画笔,来来去去不停顿,相拥翻滚着的泥巴,画出一根根加粗的线条。深犁过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和春天的气息。
从这一天开始,村里所有的牛都在田地里开疆拓土、发力耕耘,它们就像走向战场的士兵,勇往直前、奋力冲杀,直到所有田块都种上庄稼。春耕期间,牛承担了人类无法承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为了节省牛吃草的时间和体力,抓住牛耕田的空隙,抓紧收割青草,准备精美可口的饲料,然后一担担送到牛的面前,供它进食。劳累了一天的牛很会惜力,它站着把青草等饲料吞进胃囊,躺着反刍。牛反刍的时候,犹如参禅静修,舒缓漫长。有时候它会前腿跪曲,大半个身体窝在地上,后腿并拢伸展着,稍稍抬高脖颈,偶尔摇着尾巴驱赶牛蝇,眼睛一直望着虚空,回望它的前世今生。一头牛一生的辛苦,一个人几辈子叠加都比不上,有时想想,人再苦,能苦得过牛吗?
我离开故乡许多年后,故乡迎来了泛工业化的机器时代。随着牛的身影在田野中消逝,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我们这些曾经的牧童,一颗心依旧归属于那个缓慢的时代。与牛共处过的经历,让我的内心始终保持一方柔软,那是永远留给牛的神秘世界。后来,我偶然阅读《诗经·君子于役》,读到“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眼前又呈现曾经饲养过的那头老牛,它套着全副犁具,披着黄昏明亮的橙色,穿过数十年的时空,缓缓向我走来。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