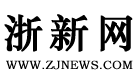陈佩君
中秋之夜,赏月,最好的去处是沈家门渔港。
我出生于渔港南岸的小渔村,这辈子就一直生活在这片海域。一年又一年,岁月的圆缺早已轮回了半个世纪之多,但那轮中秋皓月,一直如流水一般,清辉入心。
“今夜月色真美。”这句话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笔下,成为浪漫之极的经典表白。“月色真美”,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值得把这种美好分享的,那必定是所爱的人了。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总是在中秋之夜,低低地说着:“今夜月色真美。”然后就静默不语。那位老妇人就是我的外婆。我循着外婆的目光,凝视着渔港这片海域,这是一个鱼类集体睡眠的海域,安安静静,但银光的波纹似乎在水面上发了芽,一节一节地长出来,海面越来越亮,于是外婆的眼也银光一片,我知道,外婆在回忆遥远的往事。她二十八岁就守寡了,一个人将一群子女拉扯大。据说中秋那天是我外公的生日,他曾是这一带有名望的商人,高大俊朗,这从家族后辈男丁的长相可以验证,尤其是外孙的外貌简直就是外公的翻版。外公一定是外婆的最爱,她这辈子就是守着外公的血脉,支撑着这扇厚重的家门。某天,我读到一句外国诗歌:“如果把圆圆的月儿按个柄,就是一把团扇。”突然想到我的外婆,非常伤感,那圆圆的月儿是我的外公,那柄儿就是我的外婆。天上人间,团圆好难,幸好还有今夜的月色很美,陪伴望月的人儿。
“这癞头月饼咋噶好吃?”记忆中,弟弟欢天喜地的声音会在此时响起。一轮圆月在那如新烧的黑釉瓷质穹隆之上,弟弟那贪吃的嘴,张得如十五的月亮。那一层层碎碎的月饼皮屑儿,一抹又一抹,如几条长长的雨线,从弟弟的嘴角边漏出来,他慌急慌忙地一手拿饼往嘴里塞,一手拦在下颌。那时,中秋最美味的就是这款“癞头月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秋那天能吃到月饼,那种美味,那种幸福,只有那个时代的孩童才会产生同感。月饼除了那几天可以见到外,其他时间段,难以见到。而且,那是要凭粮票才可以购买的。月饼甜香啊,光闻闻那香味儿,仿佛哧溜一下,已经入嘴,连口水都无比甜香。咽着口水,我小心翼翼地将月饼捧在手心,开始一点一点地小口吃,月饼的皮会一层一层脱下来,恍如浓密的头皮突然变“癞头”,也像脚底脱皮一样,所以大伙儿还叫这款为“脚底皮月饼”。名字不太雅观,但味道真好,外皮酥脆,馅子有甜有咸,有荤有素,其中“苔条月饼”是经典代表。我们沈家门人称苔菜为“苔条”,苔菜偏咸,属于海鲜味,又被一层甜馅包裹,品尝起来别有一番滋味。酥酥脆脆的“癞头月饼”与黑色夜空中的玉盘清辉,在我记忆里慢慢演变成漫长岁月里的淳朴段落,是食品匮乏年代里的甜美记忆。
“梭子蟹上市了,桂花香了,八月十六大潮汛,也到来了。”按老话这么说,八月十六是“大节肯”(大节日)。舟山人过中秋是过八月十六的,往往这天会碰上大潮汛。我记忆中的沈家门渔港海水总是要漫上来,那些岸上的渔船总是想爬上码头,岸边的店家摆放着一包包装满沙子的麻袋,拦截入侵的海水。沈家门与鲁家峙渡口的浮桥也被海水淹没了,只好搭起了临时的木过道,一般是将长条椅一条条连起来,大家颤颤巍巍地踩着过去,然后登上渡轮。但即便是海水倒灌,我们岸两边的居民还是喜欢此时逛沈家门夜市,看海上升明月的渔港两岸。天上一轮皓月,地上满是银光。而另一些古老又永恒的美好通过这月圆的时空,恍如大潮汛的涌动,通过海的密码,来到我们的身边。
一岁又一岁中秋月的轮回中,沈家门渔港早已蜕变成时尚的模样,现在不会再出现海水深深地漫上岸来的情形。但从海的大潮汛里似乎碾出某种药物,把岁月积淀的历史还给我们,治疗渐渐流逝时光里的所有遗憾,包括莫名的忧伤。
岁月终是渐行渐远。外婆不见了,尽管我们依然说着“今夜月色真美”;“癞头”月饼也已默默退于某一角落,更多美味月饼精彩纷呈。当然,海的大潮汛还是如期到来,但渔港两岸的摆渡船早已销声匿迹。只有月亮——中秋的月亮,还是认得出那棵桂树,它仿佛来自遥远又近在咫尺。一切又是澄清又澄清,生活如是反复。
今夜月色真美,这人世间的清亮,就在我的家乡,沈家门渔港的上空。
来源: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