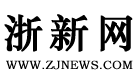陈连清 /文
棕榈树是棕榈科常绿乔木,叶近圆形,像一把大伞撑着,亭亭玉立,风度翩翩。它是个大家族,有2600余种,在我所生活的浙东一带,生长的多为毛棕、山棕和密棕。棕榈之名始见于先秦《山海经》中的“石翠之山,其木多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释名棕榈,因皮中毛缕如马之鬃毛,音同,故名。
早时家乡制作蓑衣用棕榈,实际上是用棕榈叶的棕片。棕叶长在树上,上部分是像蒲扇一样的绿叶,下部分是包裹着树干的棕色纤维。家乡把叶的下部分称为棕榈,实际是简称,大家都这么叫,也就约定俗成了,比如去买棕榈纤维就叫买棕榈,取棕榈纤维叶片叫剥棕榈。高高的棕榈树,人们通常要架梯爬到上面才能作业。随着叶片的生长,棕榈纤维会逐渐形成“网”包裹住树干,中间有一根梗,宽宽的,淡黄色,下大上小,与纤维一般高。
剥棕榈是用一把小刀自棕榈梗的一旁从上到下划下来,再在纤维和树干的交接处划切一个“圆”,使其脱离开来,斩去上部分的“蒲扇”,一张棕榈就剥下来了。接着要晒干、去粉、分类,色泽好、纤维密、修长的棕榈纤维用于蓑衣正面,次等的用于里子,材尽其用。后来用于制作蓑衣的需求减少,就转向做棕扫帚、做地毯、做船用绳索,也有用来串棕绷床,“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编蓑衣的人看到棕榈,就像是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心里喜滋滋的。家里能种上几株棕榈,那是很得意的。当年没有大规摸成片种植,是因为政策规定的限制。编蓑衣需要大量的棕榈,自家满足不了,怎么办?于是棕榈变成了商品,可去集市上买,若还是不够,人们便利用农闲时节,进村入户去买棕榈。
我曾和发小去过本地的山乡,如大闾、岙环、青屿、坞根等地,也去过邻县乐清大荆、雁荡等地,三五成群,一路吆喝着去买棕榈。那年我们去大荆买棕榈,天没亮就出发了,步行至温峤青屿再到湖雾、水涨,跑了几座山岗。看好了能剥的棕榈树,再去村里找主人,把主人叫到山上,谈好条件,便上树去剥。中午时分,拿出带来的几个糯米饼,在湖雾街要了点开水,就狼吞虎咽起来。下午在大荆山乡转了几个很陡的山岗,至夕阳下山,好不容易买足了几担,每担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回来的路上,我肩上磨破了皮,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有同伴就加快速度,把担挑到前头,歇下来,再返回将我的担接过去挑一段。挑挑歇歇,我们轻轻地吼着“哎嗬啊嗬”,一路挥汗,到家已是精疲力竭,身子像是散了架似的。
还有一次,我跟随六七人一起去玉环采购,夜里出发,步行至藤岭已夜半,到玉环城里天都放亮了。随后到陈屿,深入山区的旮旮旯旯叫买。“棕榈卖伐棕榈哦”的吆喝声回荡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到了蝤蠓岙,才放声叫了半句,后半句戛然而止,忽然看到一个曾在温岭读书我认识的女生,脸上一阵火烧,立马像做特工似的把身隐到树旁。其实心里清楚,那同学眼睛余光已扫见我,怪不好意思的,这一躲也无异于掩耳盗铃——那时做这种事也有点偷偷摸摸的。算是过了一关,溜到比邻村庄,吆喝声依旧。价钱得反复谈,多次拉锯战,如有一家谈妥价格,其他同伴就架起梯子,像猴子上树,三下五除二剥个精光。我手笨,只能旁观。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劳作,每人一担重百斤的棕榈已买好,心里乐开了花。这时同伴说,晚上要借宿农家了。我心里犯嘀咕,这穷乡僻壤的向谁去借宿?想不到山乡农民很好客。我们来到一户人家,房子的外墙是用小石子砌的,主人五十开外,听我们说要借宿,就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苦,出门人难啊,就来吧”。这一家人打水、烧饭、置被褥,忙开了,如是自家客人到来一般。当晚,主人烧了一大锅的红薯和马铃薯,我们吃得十分香甜。时至今日,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夜晚,山沟里这户人家的昏黄灯光和主人可掬的笑容。
回程可艰难了。百斤重担从陈屿挑到玉城就已叫苦连天。接下来是挑一段歇一会,如有手扶拖拉机经过,就好说歹说搭乘上一段。我也不知是怎么到的藤岭山下,俗话说“藤岭腾半天”,岭,又陡又长,每上一步都要竭尽全力,像老牛耕地喘着粗气。就这样艰难攀爬,浩荡队伍一路向前……
买棕榈的日子,虽是短暂的,但它给我的启示却是多方面的。那个年代,我的家乡人多地少,没饭吃,逼得家家户户去寻找门路,于是“逼”出了蓑衣生产的行业。编蓑衣缺原料,那就本地村镇、邻县山乡到处去寻,棕榈原料也就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水乡小镇。而我,经受过了买棕榈的磨炼,培育了韧劲和能力,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去实践,或许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能。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