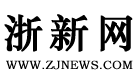特约撰稿 蒋乐平
上山,是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现上山村)的一座不知名的小土丘。2000年秋冬之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队在此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定名为上山遗址。
上山遗址遗存以大口盆为典型的夹炭红衣陶器和以石磨盘、石磨棒为典型的砾石器及石片石器最具物质标识性,经碳十四年代初步测定,遗址年代距今11000年至8600年。2005年,这一遗存在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再次被发现。2006年11月7日,在浦江召开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这种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文化”。从此,具有这一区域文化特征的遗址均被称为上山文化遗址。
2007年至今,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4处,分布于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地。遗址的分布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区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上山文化的最大发现当然是稻作遗存,袁隆平先生为之题写:“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2019年,在良渚文化申遗成功的鼓舞下,从浦江县开始,浙江省和金华等上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市、县开始推动上山文化遗址群的申遗工作。2021年11月进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稻·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和2022年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申遗”,更是将上山文化的知名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上山文化社会影响力逐渐提高,如何准确地向公众传播上山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科学问题。“万年上山稻作之源”,有资格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这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何等重要的地位啊!
社会影响力提升了,社会大众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大家对上山文化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所承担的文明符号价值,既感到兴奋,也有一些疑惑之处。其中最容易被讨论的就是上山文化“最早”和“起源”这两个关键用词。
“最早”是“起源”的前提。但所谓的“最早”,往往具有时间的局限性,比如7000年河姆渡也曾冠名“最早”。那么,应该如何去解读上山文化的“最早”和背后的“起源”问题?首先需要澄清的当然是年代。
关于年代
年代是上山遗址、上山文化的基本支撑。
年代很重要,但年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暂不去与其他早期新石器遗址比较,先来谈谈上山文化的年代。
最早的一批测年样品中,上山遗址最老的一个校正数据是公元前9400年,也就是距今11400多年,但碳十四测定数据是有误差率的,准确地说,这个数据有94%概率的置信范围是在公元前9400年至公元前8450年间,也就是距今11400年至10450年间,中值年龄约10900年。其他数据大多比这个数据晚,但分布范围基本落在10500多年到9500年间。
想要理解碳十四数据,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碳十四的测年原理。碳十四测年法又称放射性碳定年法,基本原理是根据样品中的碳十四原子衰变率计算样品的年代。碳十四作为一种放射性元素,均衡地存在于自然界各类生命体中,一旦生命体死亡,碳十四就会因衰变而降低,每经过5730年,碳十四原子就降为原有水平的一半值。通过考古样品(动植物亡体)中存留的碳十四放射性水平与它的原始放射性水平相比较,就可以算出其死亡的年龄。
从理论上说,碳十四断代法及其升级的AMS技术测定年代,并通过树轮校正,可以将测年精确到3‰~5‰,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古样品在野外提取及实验室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这种污染,如对木质样品中的草根、腐殖酸和碳酸盐的清除,存在着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另外,实验环境中的温度、大气压变化、电子仪器的差异等因素也会导致各实验室之间的系统性误差。凡此种种,均可能影响样品测年的准确性。
需要注意的是,测年所指的是样品的自然死亡年龄,并不代表其作为文化遗物的年龄,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比如从原始森林中捡来作为柴火的枯木,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死亡了。那么用该枯木样品测出的年代数据,只是树木死亡的时间,而不是利用它作为燃料(成为木炭)的真实时间,该样品的测年数据也就不代表确切的文化年代。
上山遗址是用夹炭陶片测年的,虽然夹炭陶片中掺杂大量的稻遗存,但陶坯中含量最多的当然还是泥土,那么泥土中是否包含了死亡很久之后才被掺入陶土的炭质呢?理论上很难排除这种可能。学术界对此有疑虑。这也是我们谨慎地看待11000多年数据的主要理由。
一般来说,生长期短的有机物质,比如一年生的炭化稻米,测年精确性高。因为炭化稻米的年代可以视同为它被种植的年代。
那么,上山为何不用误差率更低的炭化稻米作为测年样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山文化早期遗址,经过发掘或试掘的目前只有上山遗址和庙山遗址,而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很少或没有,有限的几粒成为重要文物,十分珍贵,舍不得作为测年样品。第二个原因是怕出现概率性的测试误差,那就白白浪费了。
目前,我们在描述上山文化的最早年代时,一般采用“距今约10000年”的说法。除了上面的分析原因外,上山文化的分期及其系列性的测年数据也是重要依据。
我们主要根据陶器的类型变化,将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相对于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年代测定更为可靠。因为中晚期已经采用了炭化稻米作为测年样品,误差率很小,而且得到足够数据的相互印证。桥头和湖西等遗址,我们在地层中浮选出较为丰富的炭化稻米,这为测年提供了条件。从中晚期的测年数据分布看,中期的年代在距今9000年前后,晚期的年代在距今8500年前后。那么早期的年代早于9000年是肯定的。以500年为一期,早期年代上限也超过距今9500年。何况,早期的测年数据也是实验室得出的真实数据,允许谨慎对待,但不允许轻率否定。
目前,属于早期的上山文化遗址有上山遗址、庙山遗址,还有一个老鹰山遗址。上山遗址存在早中期的文化叠压关系,庙山是较为纯粹的早期遗址,试掘中没有发现中晚期堆积。老鹰山遗址没有经过试掘,但现场调查采集到的陶片均具有早期特征,这三处遗址的测年均在万年前后,即使采用误差范围的下限数据,也大都超过了9500年。
这是我们将上山文化年代范围定在距今10000年至8500年间的依据。但10000年至8500年是偏向于学术的年代分析,当涉及碳十四测年的客观介绍时,也会采用距今11000多年的数据。在不同的语境中,还存在两种介绍方式并用的现象。
关于最早
2006年上山文化命名时,将上山定为“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见“最早”有具体的定义,既有外延,也有内涵。今天,我们说上山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稻作遗存,内涵变丰富了,外延也就缩小,因为包含稻作遗存的遗址只是众遗址中的少部分。“最早”也就有可能从“长江下游”拓展到“世界”。
这实际涉及语义逻辑问题。内涵与外延是概念的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越深,所包含的属性就越多,属于这个概念的个体就越少。概念的内涵越浅,所包含的属性越少,属于这个概念的属性就越多,外延越广。
关心稻作起源,尤其是关心上山文化稻作起源地位的社会人士都会注意到,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更早的稻遗存方面的信息,并且也被称之为栽培稻。如何看待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结论?
首先,这两个洞穴遗址发现的稻遗存信息存在一定的学术争议。比如,都称之为栽培稻,得出这样至关重要的结论,是否科学与准确?因为这两个洞穴遗址发现的稻遗存数量稀少,性质单一。这里暂且排除这些学术性争议,我们首先需要分辨和分清的是,上山的“最早”与仙人洞、玉蟾岩“最早”,是不同的概念。上山的最早是“稻作”,是内涵农业生产活动的人类行为;而仙人洞、玉蟾岩的“最早”是“稻”,只是静态与孤立的遗存信息。“稻”可能具有“稻作”潜在内涵,如果它确实是栽培稻;而“稻作”却具有“稻”所不具备的丰富而具体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是人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创造性智慧的真实记录,包含更丰富的历史信息量。
简单来说,上山的“最早”语义所包含的概念属性,具有玉蟾岩和仙人洞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后者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条件。
具体来说,上山的稻遗存信息中,包含了稻的收割、加工碾磨和食用的内容,稻的栽培也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更充分的证据。实际上,还包括旷野定居、房址环壕、工具多样性等与农耕生活相关的大量遗存信息。
主流考古界认为,农业起源作为一个涉及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命题,需要有上山这样的内涵丰富的文化类型的坚实支撑,才有可能去展示这个历史关键节点的复杂内涵,而不是一个由点及面的推测性质的泛泛符号。包括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在内的业内人士,都将考古研究作为上山“申遗”的重中之重,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加强上山文化在稻作起源方面“排他性”的概念属性。比如寻找当时的“水稻田”,比如进一步清晰聚落结构背后的社会形态等。
但就迄今的发现来看,上山文化已经是“最”符合这种明确学术指向的“最早”。
关于起源
在追溯稻作农业起源时,田野考古学所追求的证据,最直接的是稻遗存的发现,其次是关注稻的驯化问题。但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多元化,对“农业起源”问题的研判也渐趋客观。显然,要确定某个“时间点”,作为稻驯化或栽培的开始,很难。因为那必然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要找到某一个遗址,代替那个不容易确定的“时间点”,更难。上山文化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对水稻“栽培”和“驯化”的简单生物学认定,而与“农耕”“对土地的要求和管理”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更科学的研究与观察稻作农业起源的角度。
实际上,上山文化稻作“起源”的认定,正是着眼于农业起源的革命性意义。
农业起源是一场“革命”,这个概念自柴尔德提出后,已经成为共识。既然“起源”就是一场“革命”,那么,“起源”必须呈现革命性的成果。这种成果由一种既有确凿内涵又有一定时间空间范畴的、可供深入观察的“考古学文化”来体现,是最理想的。上山文化正是体现这一“革命”成果的万年样本。
从洞穴到旷野,是我们观察与理解这场“革命”的第一切入点。
开花结果,而不是转瞬即逝的烟花星火,是我们观察与理解这场革命的第二着眼点。
中国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即华南洞穴类型、长江中下游旷野类型和华北类型。其中华南洞穴类型和长江中下游旷野类型具有一定的区域重叠性,代表两个具有历史发展关系的两个阶段。
尽管玉蟾岩、仙人洞也发现了稻遗存,学术界也曾试图从“起源”的意义上去进行认识。但除了稻遗存单薄、容易引起具体学术证据的争议这一点之外,最大不足是“华南洞穴类型”并没有因为“稻”的出现改变自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穴居形态。也就是说,这些洞穴遗址没有体现农业起源这一革命性事件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洞穴类型”遗址普遍从新石器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中晚期,没有改变洞穴的生活方式。民族学资料证明,一些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的原始族群,后来又退回到采集狩猎者的行列。
正式走向稻作文明的第一个脚印,发现在以上山文化为先驱的“旷野类型”中。这是考古实证,是遗存所揭示的客观事实。在比上山稍后的时间里,长江中下游的诸多区域,包括靠北的江淮地区的一批遗址中出现相似的农耕迹象。这些遗址包括以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洞庭湖西北区遗址群、以城背溪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干流沿岸区遗址群和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遗址群。江淮地区这些早期农耕遗址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但“最早”的上山文化无疑是东亚大陆开启农耕文化时代的“革命性”标志。
上山文化遗址群也是早期农业遗址中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遗址群。这证明在稻作农业诞生的背景底下,所属族群在长期定居的基础上获得了壮大和发展。具有抽象图符内涵的彩陶艺术的最早出现,也体现了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先进的知识体系、观念形态领先一步萌芽、诞生的文化现象。
遗址群的规模是上山文化最重要的要素,它表明了一种新颖经济关系对聚落社会的一种稳定支撑,从而形成早、中、晚期的发展脉络。高起点的文化积淀,也对区域内文化的延续繁盛程度产生影响,浙江境内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正是从上山文化起步,稳步而迅速地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3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这正是上山稻作农业“起源”的题中之义。
来源: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