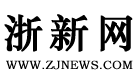施炜君
舟岱大桥的入口与往大沙青坑岭隧道的交界处有条路,路边有块牌子,写有“欢喜烟墩”,往西便是烟墩地界了。我觉得起名字的是个聪明人,烟墩被冠以“欢喜”,是在古地名的韵味中,添了一分新意,这新意便是欢喜。
我与烟墩是有缘的,从小有一种欢喜,或许是因为母亲出生在那里。小时候,母亲教过我她小时候唱过的童谣:正月里,人客多,阿娘叫我去抲鹅,鹅娘话,阿拉鹅,羽毛白白肚下黑;阿娘叫我去抲鸭,鸭娘话,阿拉鸭,上唇涮河泥,下唇涮田泥;阿娘叫我去抲鸡,鸡娘话,阿拉鸡,三更墙头喔喔啼……母亲节俭又能干,记得青饼、汤圆、酿酒样样会做,特别是酿酒,蓼草自己采来,做成酒曲,再酿成清香甘甜的米酒,是需要技术与经验的,或许是一方水土所养成的。
烟墩人大多姓夏,为明朝大学士夏言后人。母亲常说,嘉靖年间阁老太公被严嵩害死时,天暗了三日三夜。后人为避祸逃到了烟墩岙,并繁衍了下来,建造了花岩庙,供奉着阁老太公塑像,以示纪念,上了年纪的人都称烟墩为“烟墩夏”,母亲对阁老太公的名是忌讳的。
以前的花岩庙很是热闹,逢阁老太公生日或逢年过节都会邀来戏班子在庙堂里唱上几天几夜,就像鲁迅所描述的社戏一样。而《盘夫索夫》是必演曲段,曾荣唱道:骂你严嵩老奸臣/横行霸道在朝中/你残害忠良有多少……定斩你奸贼老严嵩。越剧的唱腔婉约中有激昂,把严嵩骂得畅快淋漓,后人听了自然得以胸臆舒畅。
随时光荏苒,花岩庙后来成了供销社的布店,也算热闹一番,最终荒废后被拆除。为寻回失落多年的慰藉,十几年前由阿达舅舅牵头,才重新在水库边的山坡上盖起了新花岩庙,但这是缩小版的,没有了以往的气派和热闹。
烟墩是一个自然村,坐落于狮子岩山下,村舍依山而居,且民风淳朴,从不浪费一寸良田,以前人口多时,曾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因实在不方便,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迁徙下来,安置在附近的丁家山脚下。沿后溪坑上去,溪两侧依山傍水仍住着几十户人家,春夏有溪水潺潺,鸟鸣山涧;秋冬有芦花摇曳,柚子金黄。溪边几位浣衣洗菜的阿婆,看见我会招呼说:这是陌生客人嘛。我说来这么好的地方转转。有的还要为我留座,我心里会滋生一种亲切,心想:或许她们是母亲童年的伙伴,一起唱过那首童谣,溪边采过辣蓼。
烟墩的土地资源较少,就村岙前面那一片,村民们一年四季在麦子与水稻之间劳作,生活过得朴实也艰辛,所以后来很多泥瓦工匠去了城里讨生活,待农忙时回来收割插秧,忙完又返回城里,再后来慢慢地相继留在了城里,也带走了他们的子女。
西边的村口有株百年老樟树,枝虬叶茂,绿荫下,老人们像一群倦鸟,聚坐着,有时聊天,有时都沉默着,好像在时光里寻找回忆,如此一代一代地沿袭。
在老樟树南面的寨山里附近,前几年种植了上百亩荷花,与狮子岩上的大风车都成了东海百里文廊的打卡地。我沿曲桥步入荷田深处,白鹭被成群惊起,犹如走进了李清照的词里。初夏,尖尖荷花亭亭立于田田碧叶中,是一种自然至美。清风吹过,层层叠叠的墨绿带着清香扑面而来,转身则发现已被这墨绿包围,满是清凉和惬意。
舟岱大桥在远处横跨而过,甬舟铁路也将在左侧穿山而去,烟墩像是一座被忽略了的村落,但忽略中有一种安静,村西北靠近马目有十里桃花会年年开放,给你欢喜。
来源:舟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