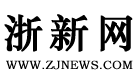那秋生
“先天不足,从兄学习,乳臭未干,舌耕糊口,汤染试卷,赴京赶考,福建候补,债台高筑,毅然返里,临浦才子。”这是关于蔡东藩一生的40字传记,这里的每一句都有曲折的经历和传奇般的故事。
蔡东藩(1877—1945)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自1916年起用十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十一部总计700万字的历史通俗演义,合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1920),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中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世界历史演义之最。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可见“演义”是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也就是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蔡东藩就是一个天生的“演义”大家——“胸中展良史才,腕底走梦笔花”。
抱着“演义救国”的素志,蔡东藩决定用自己的文史知识和笔墨才华写出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用以警觉民众,振奋精神。他说:“窃谓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据《中等新论说文苑》)
他以一己之学诉之史笔,借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人物事迹,用通俗演义之方法宣传教育,以期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操,这也正是一个书生“精忠报国”的生动表演。他是以“演义言志”,将历朝的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映照与讽喻,“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他尤其讴歌历代忧国爱民的志士仁人,激情颂扬那些拯救国难的民族英雄,使通俗演义成为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方式。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不能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但是作品的历史价值显然要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所谓“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作为“演义”自然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
蔡东藩的通俗演义,结构以章回体的形式,前有自序、中有批注、后有总评,真是蔚为大观,他居然将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合为一体了。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解释了写作《史记》的缘由与经过,蔡东藩牢牢记住了其中的三句话。一是“述往事,思来者。”治史必须鉴往知来,做到古为今用。二是“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治史需要讲究方法,如综合、归纳、分类等。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治史应当独立思考,放射出自己的眼光。
难能可贵的是,蔡东藩正确运用了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努力写好自己的“演义”。他自幼爱好历史,熟读传统的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入研究,甚至养成了“考据癖”。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他常常能做到多方钩稽,并灵活处置:或一味地寻根究源,力求找出客观真相;或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的,就诸说并存;或一经认定的史籍中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临浦才子功成名就了。
据说,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他知道不在,就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后来,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件事的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与‘共和’!”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暴力面前是决不屈服的,这正是“会稽风度”——文人名士的铮铮铁骨。
作者系绍兴越文化研究者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