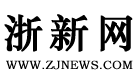范泽木
以前看书不太喜欢看序言,直接翻到正文,再火急火燎往后看。现在,我却对一本书的序言珍惜起来。
序言让我觉得亲切,拉近了我和作者的距离,也拉近了我和文本的距离。有一些序言讲的是创作动机,言简意赅,玲珑剔透如一块吊坠。也有一些序言,洋洋洒洒,谈作者创作风格的流变,谈国内外创作前沿,林林总总,体量庞大。总而言之,序言如桥,给了我避免涉水过河的方便。读钱钟书主编的《宋诗选注》,有杨绛先生写的代序,讲钱钟书为文为人,又有钱钟书自作的序,讲选诗标准及唐诗到宋诗的变化与传承,浓浓的学术味。前者如叙家常,后者正襟危坐侃侃而谈,读之,颇得趣味。序如宝藏,读之,往往有会心处。
我的看书方式也有了变化。以前总是从头至尾,一板一眼,看起来态度端正,读书收获多少,唯有自知。多年前我捧着《红楼梦》读,但前两章就是拦路虎,把我难住了。后来竟没有拿起此书的勇气。大概到了2021年或2022年,我又捧起《红楼梦》。这一回鬼使神差,随意地翻到了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当时也是正月,元宵节刚过不久,读这一回,很是时候。读着,竟一发不可收,闲时捧着纸质书读,条件不允许时就拿着手机读。一直读到全文结束,再回过头补读前十六回,终于把全书看完。读完,心里闷闷的,余音绕梁好多天。
三四年前,买了朱西寗的《旱魃》。序言是莫言写的,他赞叹朱西寗那么早就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大有读之恨晚的意思。我读兴高涨,可读了不到万把字,就被里面的人物关系难住了,加之朱西寗在写作时用了不少方言,让我举步维艰。今年夏天,天热,且热得持久,心里老想到《旱魃》一书。那日翻书,一翻就翻到了佟秋香和佟老爹及皮大爷去红马埠杂耍,半路上遇到拦路贼的情形。读之兴味盎然,一口气读了一万多字,才晓得作者用的是倒叙和双线索叙述的方式写作。我无意间翻到的,恰是故事的开头,这无疑让我的阅读之路顺畅了许多。和读《红楼梦》一样,我也是看到了结尾再来补看开头。整个故事了然于心,畅快不已。
有了这两次经历,我看书也就不那么一板一眼了,随意地翻,总能遇到新奇处,然后顺着这点意兴读,直到把整本书读完,如拆盲盒,多了许多紧张与刺激。
读张大春的书,我第一次知道了接驳式阅读,其实就是用书来串连书。那本书提到“江南八侠”甚多,我读完后就读了陆士谔的《八大剑侠传》,结果又读了陆士谔写的其他几本书。如此,以书找书,书自己会开书单。大概七八年前,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听白岩松的一场讲座,他也提到以书找书的观点。
今年春末,读胡竹峰《惜字亭下》一书,得知他对木心和汪曾祺推崇得很。于是,我看了木心的《素履之往》及汪曾祺的《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汪曾祺散文》。汪曾祺在散文中提及包括他的恩师沈从文在内的诸多大家,与他们的过往被写得妙趣横生。于是重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又预备看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作品。以书找书,实在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读书如逛古民居古村落,推开一扇门,里面别有洞天。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