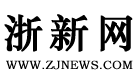缪菊仙
早晨六点出小区,去月亮湾公园晨练。迎面朝霞旭旭,紫薇低垂,高大的合欢疏朗的枝叶间挂起一串串黄褐色的荚果,随风摇荡,零星的几朵绒花浮在枝头,有美人迟暮的寂寥。黄山栾树一展芳华,枝头黄灿欲燃,微风一过,不时有小黄花簌簌而落。一辆脚踏小三轮缓缓经过树底,落花跳在骑车人的斗笠上,黄花红蕊,金色的霞光加持着,别样明艳,别样安宁。
小三轮被一位晨练的行人叫住,“编织袋里是玉米吗,要卖不?”“要的,我拿到超市门口去卖。你要买,那就这里吧。”小三轮停在黄山栾树下。其实,被叫停的不是小三轮,不是骑车人,是车内编织袋里裹着碧绿外衣、沾着露水的鲜嫩玉米。
卖玉米的是一位老人,花白头发,黢黑发亮的脸上布满皱纹,看着却很舒展,深蓝色短袖上衣敞开着,短裤拖鞋,小腿结实,微微佝着背。老人有条不紊摆开电子秤,端出二维码,扯开编织袋的袋口,将碧绿的玉米棒“呼啦啦”倒在小三轮里。三五行人围了过去,一边问价格,一边褪去青绿的玉米外衣,扯去玉米须。“不用翻,每一个都好的,早上五点多刚离了地呢。”“老嫩看胡须,颜色深的是老一些的,浅的是嫩一些的。”老人卖玉米,又护玉米,他看着买家翻来翻去挑选,很是着急,很是心疼,玉米如同他的孩子,他不愿它们被挑三拣四。
我也上前,听老人夸他的玉米,说自己种地的不易。“我八十多岁了,身子能动,地不能荒的。”“今年旱啊,这玉米是每天浇水浇出来的,你看这籽粒饱满的。”“我用的菜籽饼,鲜甜鲜甜。”五元一斤的鲜玉米,实在是低于市场价的。电子秤上的价格是老人子女设置的,二维码是从邻居处借的。每收一笔钱,老人都仔细听一遍语音读数,拿出一个本子记一记,说自己要记清楚,回去得和邻居结现金呢。
听到老人嘴里吐出的“鲜甜”两字,我鼻子猛一酸。“鲜甜”曾是父亲的口头禅,是他种的菜与瓜果的广告词。我想起父亲的晚年因为种地卖菜而年年遭我“打击”,被迫写下“不再种菜售卖”的保证书,后因故态复萌常常被我数落。那时以为,我有能力让父亲衣食无忧,他就应该放下他钟爱的锄头扁担,穿着整洁的衣服在村里转悠,适时夸夸子女的孝顺。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依然身体康健,依然不顾我的反对,早出晚归在地里搞创收,走街串村叫卖他的有机时蔬,晚上回家,灯下财迷样数钱,嘴角上扬,眉头舒展,这是属于他的快乐时光。年老的父亲走在夕阳里,认为“田地是甜的”,他用岁月耕耘,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土地的执着与期盼。
什么是安享晚年,什么是孝顺,直到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这个卖玉米的老人,这个和父亲一样喜欢劳作的老人,我相信他也是衣食无忧的。劳作是本能,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我是有用的”,这样的精神需求比养老金重要得多。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经常在朋友圈晒她与九十高龄的父亲在地头劳作的图片,她的父亲阳光底下灿烂又满足的笑容让人动容。同学用行动支持父亲的土地事业,是一种“顺”字当头的宠溺,她给了父亲劳作的快乐、生活的尊严,为我解读了“孝顺”,并不仅仅是我以为的给钱给物。
一波交易小高潮,编织袋空了一半。我拎着玉米回家,回头看老人,正佝着背,眯着眼,一丝不苟在本子上记账。霞光洒在老人身上,老人的侧影和小三轮熠熠生辉。看到这样的侧影,莫名喉咙发紧,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对在时光里走远的父亲深深歉疚。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