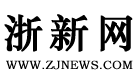柴薪
一早起来去沙湾,一路上已经没有昨天清早时的暑气,凉风吹来,凉爽宜人。真有唐代诗人司空曙的“向风凉稍动”之况味。昨夜的一场大雨,把沙湾的一切淋透了,气温降了下来,沙湾也像是突然静了下来。被雨淋过草木似乎也精神起来,树木的叶子一身碧绿,飞蓬草也挺直了身子,天空那么蓝,白云那么白,树丛中的鸟鸣声那么动听,像水洗过了一样,一切仿佛是崭新的。
立秋之后,虽然太阳依旧很大,很亮,很热,但这种热有点薄,有点浅,有点淡,盛夏时的那种热力,持续、锐利的酷热不见了。在清早,吹在身上的风,也是凉爽的。
站在沙湾的空地上,举目四望,草木的景致似乎也和以往不同了。似乎没有了春天的苏醒、蓄势待发,夏天的勃发、欣欣向荣。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我知道,秋天就要来了。不知为什么,不只是草木,有些事物,也会莫名地给我某种秋天的感觉。比如,一个地名,长台(我出生的地方),衢州(我生活工作的地方),比如,沙湾(我现在每天种菜的地方)。
太阳出来了,今天的太阳是白色的,照在菜地上恍惚而耀眼。
立秋之后好多天了,但太阳依旧很大,很亮,很热。我给豇豆松了土,施了复合肥,浇了水,做好这一切,头上已蓄满了汗水。老邵过来,给了我四根刚摘的丝瓜,并告诉我拿来炒好吃,炒时不要放水,出锅时加一点生抽、白糖,更好吃。
我走到菜地边的樟树下,从塑料袋里拿了毛巾擦汗,坐在树下喝水,休息。一粒果子从空中落下,掉在地上的白铁皮上,发一声坚硬的脆响。一阵风吹过,树叶“飒飒”作响,风越吹,声越响,一阵一阵,一阵高过一阵,其中还夹杂着头顶飞机掠过的轰鸣刺响。风也从我头发上吹过,从我脸上吹过,从我身上吹过,从我湿透的短袖上吹过,一阵清凉。
风吹过来,又吹过去,我不知道,风会吹向哪里?
风中,望着头顶婆娑的树叶,我突然想起我风中摇曳的故乡,想起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想起兄弟姐妹。我们这代人,不管其他境遇怎样,还是有福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兄弟姐妹,拥有这种天生的同一血脉的骨肉亲情。不像独生子女这一代,很多东西是无法比拟的,也是无法体会、感受的。我又想起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许多人已经好久不见了,从我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没有想到,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分离,天南地北,各奔东西。许多东西只能回忆了,而回忆中的一些碎片,也是少年时仅有一些片段,大多场景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成年后的经历,或一帆风顺,或千疮百孔,或沧桑历尽,就像从我身边吹过的风,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大多都不知道了。
也有少数几个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他们甚至最多只去过县城。他们大多是一些残疾人,比如聋哑人、驼背、疯子、傻子、瘸子、盲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我是认识的。
聋哑人很聪明,他能写出我们所有人的姓名,知道我们的年龄,知道我们兄弟的排行,他什么农活都能干,而且干得很巧,喜欢钓鱼,是个钓鱼的好手。驼背老实,放过牛,镇里脾气最凶、最猛的黄牛在他面前都服服帖帖的,都听他的话,一点脾气都没有,我甚至怀疑他通牛语。驼背还拉过算命人(盲人),在各个乡间游走。疯子不疯的时候,会烧饭,会喂猪,会到河滩上捡柴火,后来,游泳时淹死了。傻子原是个棉花匠,我见过他给人弹棉被。傻子烧菜切肉时,人家是用刀切的,他是用剪刀剪的,烧好的肉,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后来,一次离家后,不知所终,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个傻子,话多,且到处乱说,乡人不以为然。有一年嵩溪河发洪水时,他从桥上跳入河中。被洪水冲出了十多里,在昭明桥附近,他被河边的柳树枝勾住,被人发现后救起。从此以后,沉默寡言,不言不语,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瘸子是个女的,肤白,貌美。我少年时,过年时到镇尾舅公家拜年时都能见到她。阳光照在大柿树厚厚的叶子上,溅到她的脸上如花绽放。后来,瘸子跟人学了裁缝,后来,听说嫁到近邻的福建浦城去了。盲人穿街走巷,游走乡间,为人算命,自己的命却在风中飘游。
在故乡这一片空空的土地上,有过他们生命的沉寂与呼喊,有过他们生活的苦难与无奈。他们虽然是不幸的,却都顽强地活着,或无声地死去。
他们从出生后就没有离开过故乡,但某些方面或许比那些离开故乡,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人幸运或幸福。
逝水流年,我不知道,风会吹向哪里,也不知道风最终会把我吹向哪里。生命在天地之间流转,并且波澜不惊。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