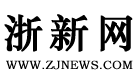陈连清
1962年至1968年,我在原温岭莞渭小学读书。
那时的课程简单,就是语文、算术,还有音体美劳。我觉得学习很轻松,作业都能当堂完成,很少带回家做;老师提问时,我总是抢先回答。
当时老师给学生打分是5分制(学习成绩的等第,不是现在大学里要修的学分),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门门都是5分。成绩单送到家时,左邻右舍争相传阅。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心里有点小得意。
除了赚学分,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会学着父辈的模样,参与农活挣工分。
只要遇上队里劳动,我们就把星期天和暑寒假交给田野。我所在的是原温岭观渭陈大队(今莞渭陈村)第六生产队,队里人均四五分土地,社员一年只要三分之一时间在田里劳作就足够了。农闲时,或从事副业串蓑衣,或在河里拔鱼(一种围网捕鱼)。
那时,队里实行工分制,就是按社员提供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记工分。最高为10分,相当于一个企业里把关的工程师,往下依次降低。队里每年在夏收前都要对每个劳力重新评定一次工分,我还记得评工分时的情景。
夏夜,满天星斗,银河斜挂在头顶,道地上点起一盏昏黄的菜油豆灯。大家围坐一圈,互相点评。我本以为这个评分嘛,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得了。谁知,每个人一丝不苟,分清露白(分出细微的差别),指出哪一点是好的,哪一点不行,有理有据,实事求是。最后根据讨论的内容,评出等分,还评出小数点下的数。农民这种朴实求真的品格深深感动了我。
我的一个堂叔算个文化人,保管报纸,为队里记工分,兼作会计。他做起事来总是慢一拍,社员们七嘴八舌给他评了8.6分。这个分在成人中算是低的。那一晚,他像吃了一顿重庆火锅,又麻又辣,吃得面红耳赤。
我们这些小学生自然是排在尾巴了,有几个同学被评为3分,而我只有2分。我仰望星空,这天上星星都在对我眨眼,似乎在说:“你有不足嗬,要奋起直追咯!”
2分是最低的,因为我的表现比其他同学要差一截。斫草子时速度没他们快,割稻几次割到手指上,学车水常常被“钓鳗”(荡在空中)。
我第一次参加劳动是给冬田里的草子施灰肥。那时的草子是苜蓿,一丛丛在田里种成一行行。待到春耕时把它们割下来,剁碎用作早稻的主肥。施灰肥是将灰施于其根部以利于吸收。而我做得毛糙,灰放得不到位,受到大人的批评。
春耕之后就是插秧。一次,我跟在大人后面插秧。大伯发现我的秧短一些,于是将我插好的一株秧拔起来,发现插下去的秧苗是弯着的。大伯说这是因为我的手没有捏住根,而是抓在秧的腰部往下插。平时待我很好的大伯,顿时咆哮起来,叫我重来。有社员开玩笑说:“你是白脚梗,应去坐办公室。”有人讽刺道:“这个人看起来长长度度(高大),实际是一株胖杉树。”我知道后,脸上红一阵热一阵。
后来,我琢磨一个问题,为何懂得点文化的人,在田间劳作时会比别人差一截?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关心天下大事,也喜欢读些书,这样一部分精力就分散了,农活当然也可以学会,但其兴趣点不在这里,于是对一些重体力和高技能的农活用心较少,因而就显得弱些。到了田间,他们喜欢做宣传员,在给人带来一些欢乐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干农活的质量。我发现,田头讲三国故事、唱田歌的,工分都不会很高。所以,要想做好一件事,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在田间劳作时,每个人都是一个农民,高效做好手上的事是自己的本分。
找到原因,到了初高中参加田间劳动时,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克服“小猫钓鱼”的心态。在拔秧插田、割麦打稻、挑担施肥、犁田耙田、捻河泥等农活中,我专心致志,舍得用力,锻炼恒力,尽显自己农民的角色,当我在捻河泥的船舷上站稳脚跟时,就成了一个能挣10分的社员了。
来源:台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