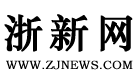彭艳艳 /文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者迟子建,书成2005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弱小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风情。
“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这位年近九旬、不擅长说故事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用苍老的声音,从她自己的诞生开始,缓缓讲述乌力楞里的人与事,一个家族整整五代人,历尽生命中的苦难与绝境、爱与希望,关于自然,关于人性,关于民族,关于社会。
本书共分四部。上部《清晨》,以“我”出嫁前的清澈视角,展示鄂温克人敖鲁古雅部落的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原始森林,从一片山游牧至另一片山,靠猎物与外来安达以物换物;乌力楞的一大家子,个性鲜明,敢爱敢恨,感恩自然,敬畏神明,自给自足的生活虽有各种小插曲,但快乐又美好。中部《正午》,日本人来了,来自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娜杰什卡走了,平静的森林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猎户被迫下山参加日本东大营集训,“我”在饥饿困顿中遇见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在分娩阵痛中窥见上辈人的疼痛爱情。下部《黄昏》,“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是最后一个酋长,大家温情守护部落族人,但是几个乌力楞分分合合,生生死死,被时代撕开缺口的森林再也无法愈合。尾声《半个月亮》,生活在山上猎民已不足两百人,新的鄂温克猎民定居点在布苏建立,猎民和驯鹿大规模搬迁,除了“我”和爱啃树皮的安草尔,还有一只下山后又跑回家的白色驯鹿木库莲。
作者的文字优美、简洁,在她笔下,你会看到美丽的自然,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万物都是有灵性的。“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绒一样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纹。”“水中的月亮就被它拨弄得破碎了,水面上荡漾着金黄的月亮残片,让人为月亮心疼着。”你的眼前出现一幅原始森林斑驳又葱郁、月光下水波粼粼的美好影像。文字平铺直叙,但是情节却跌宕起伏,传统与文明,生存与生活,各种矛盾互相撞击,让人揪心,却也让人认识到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历史洪流引起的变迁无法抵挡。而“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只有时光,抚慰一切。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总有悲凉的气氛弥漫四周,这是跟随书中节奏慢慢蓄积的情绪。在书中淋漓尽致展现的人性,没有大奸大恶,唯有人世间的欲念冲突和因果轮回,诸多爱而不得的因,导致各种美丑的果。林克、尼都萨满共同守护达玛拉,林克死后,碍于族中规矩,两人有情却无法相守,可怜的达玛拉迅速衰老,最后穿着美丽的羽毛裙跳了一夜舞离开人世;依芙琳大概是全书中最令人厌烦的角色,因不能忍受丈夫心中有爱而看不惯一切美好,总是一语成谶招来恶果,但临死前其言也善,用颤抖的手,为小玛克辛姆抚平烂疮;三十岁了还被拉吉米当作孩子的马伊堪,空有美丽面庞,留下2岁的西班,郁郁跳崖……这些书中人物的命运像巨石一样沉重,压得人喘不上气。但故事听完,却已释然,坚守信仰与梦想,对生活充满热爱和希望本没有错,怪只怪“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迟子建在跋文《从山峦到海洋》中这么说:如果说我的这部长篇分为四个乐章的话,那么第一乐章的《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第二乐章的《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进入第三乐章的《黄昏》,它是疾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了一缕缕的不和谐音。而到了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和安恬,应该是一首满怀憧憬的小夜曲,或者是弥散着钟声的安魂曲。作者成书时的时代背景,有对过度砍伐、保护传统文化的思考,比如,“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额尔古纳河右岸》,苍凉而温暖,值得用平静的心来细细品读。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