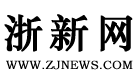任 健 /文
张广星老师很勤奋,今年年初推出了《脚印集》,不久前又有新著《一方集》出版。
显然,《一方集》书名取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广星说:“几十年的媒体人职业生涯和文学写作经历,都使我更加深爱这方土地,这方土地上的人,这方土地的一草一木。所以这里的文字,都是充满真情的文字。我爱这里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已经逝去还是健在。”他说的这一方土地,指的是家乡黄岩,也指台州,也指中国。
每个人的人生际会,都映照着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一些宏大叙事。人,不管活多长或多短,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有故事的,或悲伤或欣喜,都值得被记录。
叶廷璧、张永生、何敬业、夏矛、钱国丹、叶文玲、蔡天新、黄准……这些闪亮的名字,先后出现在《一方集》中。这是一部纯粹的“怀人录”,除了少部分写亲友、老师、同学,大部分写的是作者家乡黄岩文艺界的人物故事。张广星以良善、温润的心灵,呈现给读者月华般清辉的文字。
书中写知名画家蒋文兵和夫人施铮铮的文章共有四篇之多。写到蒋文兵艺术创作不拘一格,援引王伯敏的评价:当走笔拉线到了兴奋极点时,他是一位忠于艺术的“无法无天”者;《近佛的人》写的是施铮铮,结尾写道:在我看来,能在现实世界中看淡并放下功名利禄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佛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施铮铮老师也是个近佛的人。
认识张广星老师几十年了,但交集不多,直到前年报社和广电合并,才有幸成为同事。早年听说他抛开公务员身份,主动要求去电视台当记者,很是钦佩:他是一位懂得从理解自身天性禀赋出发,穿越普世价值观,追逐自己理想的人。在新闻业界,张老师一直备受尊重——他品性中真诚而质朴的特质,在为人处世中自然流露,在文字中更有着淋漓尽致的表达。
非虚构写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以在场的方式追忆往事,并将写作者的真情实感融入叙述。
张广星是原黄岩县府办秘书,亲历了黄岩当时孙书记领导下经济社会人心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集》中,关于黄岩老县委书记孙万鹏的专题文章有两篇,其中《黄岩好书记孙万鹏》一文,写孙任职期间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联合发文,扶持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这是全国第一个明确支持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政府红头文件。此为新闻事实。文章接着写道:孙书记对民营经济的全力支持,使黄岩经济突飞猛进。这是作者的观点,抑或是黄岩百姓的观点。事实与观点无缝衔接,没有强加于读者的生硬感,读来自然流畅。另一篇,作者从《人物》旧刊读后感引发朋友圈系列留言说起,回忆孙的日常点滴,表达了对老领导开阔的视野、清廉的工作作风的激赏和崇敬。
时光如流,在岁月悠长的回声中,那些曾经启迪、温暖、关照过我们的人,怎能不让我们一次次怀想一次次感佩?
杜甫在写给李白的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里有一句“遇我宿心亲”,意思是遇到和自己心气相通、志同道合的人,不要想着合二为一,也不要认为可以取代,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只是从此内心多了一份理解和欢喜。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欣赏这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
在《安息吧,伟雄》一文中,作者以沉静的叙述悼念英年早逝的画家黄伟雄。“他对当时的央视品牌栏目《百家讲坛》,一些知名人物讲的‘红楼’人物,常常有不同意见。他还能就《红楼梦》中的园林花卉、中医饮食、风俗描写,述说他的见解。一个山旮旯里出来的乡文化员,竟然如此博学多闻,而且凡事都有自己的卓见,这让我非常惊讶。”作者还写到一个动人的场景:“有时伟雄躺在桌子上,我也躺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们漫无边际地聊,可以聊到不知天之将黑甚至已黑。”那时,黄伟雄已辞职,在黄岩孔园文昌阁办美术培训班。周末得空,张广星经常骑车去见他。下午,送走学生,把教室打扫一下,他们就在同学们的凳子上坐下来。没错,有时是躺,在桌子上。
刘震云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试问:人的一生中,能遇见几个可以不拘小节并且很聊得来的朋友?
除了黄伟雄,还有陈叔亮、周宪文、叶春文、章甫秋、王德虎、万家超、张晖等等,《一方集》把大量的篇幅留给了逝者。张广星对那些已逝者的赞许和不舍都幻化成深沉的悲悯,内化于心后娓娓道来,似是老友间温柔的倾诉,也如史海钩沉轻轻提拉缓缓放下。如《怀念李启海老师》,写黄昏下班途中,收到短信,得知高中班主任李启海离世的消息。入题前,用了七八百字的篇幅写洪崇恩、毛昭晰、刘宗武、孙犁等人的离去,想来作者思绪纷繁不忍直入。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识人、阅读,都是遇见。金秋桂子,十里飘香。在处处流淌着柔情蜜意的时节,读张广星的《一方集》,是美好的遇见。
来源: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