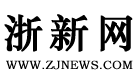梅森
城市的月光稀少,大部分是忘记停留。就像一个站在阳台上的人,通过楼宇间的间隙碰到一场日落,低矮地,孤独地着站在故乡的泥墙上将身影拉长。如果月光亮时,记忆便清晰,深秋易冷除了皮肤接受到的敏感,思绪脆弱的部分最容易结霜,镰刀切过植物的脖颈拥有月光类似的枯白,它清晰且深邃。
那个时节,我们奔赴于玉米盛大的收割,紧接着就是月光而至,但还不是饱满。留了一些日子给月亮,也给祝福,母亲说要发面,我说好。问婶子要了一把红豆,又在商店买了秋瓜,那些裹了夹心的月饼我偷偷吃了一个被母亲白了眼。一家人在院里看月亮的那晚,母亲讲了很多的故事,至此我仍旧清晰记得她说吴刚拼命砍玉桂,后面说的我怎么也记不起,也许那些人物只有吴刚和嫦娥拥有名字,其他的名字也许太平常了,她说,芳芳,萍萍,就我们村子已经好几个了,但事情发生又不是关于她们的故事,不认识的,我没了兴趣,就去看《霍元甲》。
巨大的锅盔上放着各式造型的花馍,比较常见就是狗和兔子,其实是做起来比较方便,红豆点缀了动物的眼睛,嘴巴和鼻子,我咬掉几个兔子的尾巴,母亲骂我不懂事,因这是一件庄重的仪式。“八月十五献月亮”在我记忆里是幅美景,四方的供桌上,当所有的食物被端放整齐时,月光出奇的静,停止流动,黑暗成为纯净的背景,光从黑暗里迸发出直线,直线搅动着视觉,视觉里混合着尘埃和一条条笔直的路,我从来不会在这个时刻说话,凝固的氛围让我失去淘气。其实长大就是这样,你得用眼睛和心去感受整个事物发生的过程,然后有了一种无法名状的未来并期待。我依靠着上房的木门,看着月光让新鲜的食物变得透白,我真希望可以看到吴刚砍伐玉桂,这样这个故事就会在之后消失,这样占据内心的其他故事就会多一点,而不是只要一开头就说,甚至带着母亲的口气:“月亮上有个吴刚在砍嫦娥的玉桂。”后来我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关于玉兔、后羿、嫦娥飞奔,但奇怪这些故事被说时缺少幸福。后来每每时刻盯着那一桌子的食物发呆,像是一座小山,堆积的情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似乎就能接近月亮一些。其实我问过那个傻问题,很早就问了,“为什么要献月饼,神仙又不吃。”我被母亲那灵巧的回答接受,“当然吃,吃了人家才保佑你。”那几个被我咬坏的尾巴,缺口在月光下异常明显。
人和月亮遥遥相望,走了很远的路抬起头就是一轮月亮。我从故乡往江南赶时,透过车窗看到饱满之月,只是那天它越亮就越掩盖掉那些星光,我便觉得月亮孤独,用极大的光亮铺盖掉整个世界,内心一定需要消耗很大的力量和勇气。
后来,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仪式,大部分时候告诉我忙碌。怎么会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仪式,月光是极好的照明,很多的收割其实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初生的露水箍住果实和皴裂的表皮,镰刀不再坚硬,茎干变得柔软,月光下倒下的植物覆盖掉收割时的嘈杂,静悄悄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团黑色的影子,没有名字,丢失呼吸,握在手中的镰刀和躯干融为一体,远远地举起的手电筒不再明亮,困乏使我胳膊酸痛,本该照明的电器一次次被举起又放下,植物巨大的影子长高又落下,我失掉了力气,而电池空虚。我审视秋天,收获太重了,它压弯了他们的脊梁,秋天用黄色描绘实在太单薄,不过是视线具体到叶落而已,看到另外的白色和黑色,是身体上的疲累,是想起之后的痛苦。
月光又到了,跟窥探到江南的秋天一样实属不易,我向来依靠身体记忆,以往靠鼻子嗅到秋天玉米成熟时的香甜,寒风使树木低吟时,我驻足良久,首先就想到冬天到了,或许写作者都有类似的敏感又或者冥冥之中期待着什么,当事情成为他们脑海里不可复制的一面时,记忆就苏醒了,所以我把这个当作身体记忆。
阿Q送给我月饼和香梨,其实我们住的地方挺近的,谈不上牵挂,说成祝福最好了,互相都没有说那些客套话,只在微信结尾留了节日快乐。
那天,我站在阳台上,举起右手握住光,举起,重复月光亲临土地时的那个动作,赞美的如同真理:
细砂无数,星辰无数,
当有一星,发光予吾?
但星辰的流转正如人世的沧桑,未必尽是赏心乐事。
来源:舟山日报